迈克尔·麦卡锡是《泰晤士报》的环境记者和《独立报》环境版块的优秀编辑,这本书的题献给他的母亲诺拉,罹患精神疾病的母亲离开年幼的他和哥哥去疗养,哥哥深受打击,而他的自保机制是将情绪全部关闭。搬去姨妈家后,他被花园里醉鱼草上蹁跹的蝴蝶摄去心魂,这是他爱上自然的开始。近结尾处写到他发起报纸选题,自己也加入,用一个夏天找到英国的全部58种蝴蝶,献给已逝的母亲,令人读之泪下。而他也属于最后一批经历英国的丰富自然时代的人,住宅附近的草坪和山楂树篱都挤满了家麻雀、树麻雀、林岩鹨、鹪鹩等十种鸟。夏夜行车,头灯光下,飞蛾如雪暴扑窗(原名The Moth Snowstorm的由来),之后的年代,集约农业造成物种多样性锐减,蛾雪暴几乎消失殆尽。这里顺便推荐约翰·刘易斯-坦普尔的两本书Meadowland和Running Hare(北京联合已出中译本),读毕可充分了解英国传统方式的农田耕作和牧草地对于保持物种丰度的重要性。
因为目睹过丰饶,所以分外敏感和痛苦于丧失。追忆往事是必须的,作者用很多篇幅描写那些极为美妙又深刻的自然体验,这种时候他真是笔力非凡。如在迪伊河口观察水禽和涉禽,“它们在泥浆、淤泥和黏稠之中挪动,永远那般优雅”;因迷醉于林下的蓝铃花而一周内连去五次,还有同17岁的儿子看到翠鸟一掠而过的蓝光,“塞布这一代人并不热衷观察大自然,但暮色里的蓝色闪光让他毫不犹豫地停下了脚步”,(写色彩的这一章“享受地球之美”绝对不可错过),他已探索了三十年的南英格兰白垩丘陵地带河流,最完美的鳟鱼河,“金酒般清冽”。
然后他从“喜悦”(还有“惊奇”[wonder])的感受出发,呼吁人们不应视自然的馈赠为当然,而应以热爱滋养信仰,珍惜并保护自然。他如此看重“喜悦”(joy)这个词的意义,在第二章“邂逅荒野”中做了精彩的辨析,我很有共鸣,摘录下来:“不知何故,这种幸福是与众不同的。它绝不是快活(fun)的同义词,甚至和愉悦(delight)也不同,与描述终极满足的那些措辞也不大一样——比如极乐(bliss)或者狂喜(rapture),在我们这个推崇讽刺的时代,大家几乎不太可能用喜悦这类词,除非是在烹饪写作里(用优质初榨冷榨橄榄油炸新鲜土豆——太美味了[bliss])……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我们用来描述自我满足的词(所以我们不会用它来描述由药物引起的感受,即使是毒品引发的最强烈的兴奋也不行);喜悦这个词看起来是向外的,面向另一个人,另一个目标,另一种力量。喜悦并不是由道德组成的,但它至少是庄严的。它所表达的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幸福感。……这种感受并不是排他的,也不是智者、有识者或者少数特权阶级的私有财产,它对我们每个人开放。” 麦卡锡在此着墨甚多,力陈一点:大自然在个体心中激发喜悦和惊奇,这是人类的本能和共性,足以证明人与自然的悠久关联。
在同一本书中,他也以资深环境记者的老练口吻,报道现实中环境遭破坏的案例,援引数据,如韩国新万金工程毁掉的河口对迁徙鸟类的致命影响,英国家麻雀的消失及其原因分析,以事实为证据,展开激情的论证,以此说服、震动和警示读者。记得小熊之前读过这本书以后,说觉得麦卡锡在这本书里好像分裂成两个人,现在我想其实就是因为这两类不同的叙事手段。麦卡锡这本书算是典型的环境书写,他有可称得痛切的现实关照,在书写策略上,也力图结合多种方式,语气有时甚至激愤,不像传统的自然文学作者往往着重于环境和生物的描写,抒发一己个体在自然中的感受,意在使读者产生美与情感的共鸣,少有说教和宣讲的成分。
回到主旨,麦卡锡在本书结尾指出“能够直达人心的只有信仰”,在对自然本能的热爱和欣赏之上,加入理解和知识,从而“拥有一种全新的爱”,一种“有学问的爱”,这些爱“拥有真正的力量”,“普通人的感受就是政治意愿的开端”。我想归根结底是要说到环境伦理这个问题,但是这无法一蹴而就。前向读《小鸟》刊登的访谈,环境史教授侯深引用最先提出土地伦理的利奥波德的一句话:”我们用19个世纪才发展出人与人之间较为体面的关系,可能需要另外19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发展出人与自然之间较为体面的关系”。当被问到该如何理解和建立人类在萎缩的星球与扩张的城市之间建立一种脆弱的平衡时,她答道:“10年前我会毫无疑问地告诉你是后者,伦理和审美是我们最重要的救赎,但随着自身研究不断深入,而且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强大之后,我已经没有办法如此轻易地说我们仅仅依靠伦理力量,依靠自身道德约束力量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又一次感慨,有明确诉求的环境书写难为,用数据和事实,用诗意优美的描述,用情感真切的深刻体验,比例如何安排,论证如何展开,如何过渡,如何交织,如何最终打动、启发、震荡心灵。麦卡锡似乎做了各种尝试,想来不同的读者都会有印象深刻的部分。对于记忆力日益低下的我而言,最终在脑海中萦绕不去的全是作者引用的诗歌,杰拉德·霍普金斯——“愿野草与荒野长存”,谢默斯·西尼——“回忆起飞流急转的河水,翠鸟在黄昏时,闪烁着蓝光”,D.H.劳伦斯——“蓝色的黑暗,散播光明,那就引领我吧,为我引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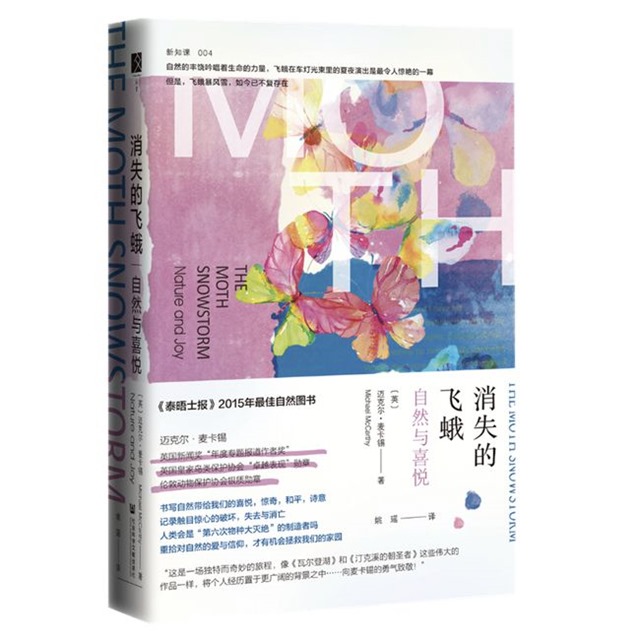
附:物种名称误译不完全名录:
- p. 36 “家雀”(house sparrow)应为家麻雀;”篱雀“(hedge sparrow)应为林岩鹨;”画眉鸟”(song thrush)应为欧歌鸫
- p. 89 “罂粟”应为虞美人
- p. 99 “绿翅兰花“(green-winged orchid)应为蓝紫倒距兰;“疗伤绒毛花”(kidney vetch)应为岩豆;“野翁”(whinchat)应为草原石䳭
- p. 105 “斜颈啄木鸟”(wryneck)应为蚁鴷;“斯维尼菊苣”(swine’s succory)应为小羊苣;“夏日兰花”(summer lady’s tresses)应为“夏绶草”
- p. 105 “大铜色蝶”(large copper)应为橙昙灰蝶,
- p. 113 “花园虎蛾“(garden tiger moth)应为豹灯蛾
- p. 162 “棕色灰蝶”(brown hairstreak)应为线灰蝶
- p. 164 “七叶树”(horse chestnut)应为欧洲七叶树
- p. 165“紫罗兰木匠蜂”(violet carpenter bee)应为紫蓝木蜂
- p. 172 “蓝钟花”(bluebell)应为蓝铃花
- p. 173 “阔叶蒜”(ramson)和“野生鸭蒜”(wild garlic)是一种东西,应为“熊韭”;查了一下原文是ramsons (wild garlic),不知译者怎么搞成了两种植物。
- p. 262 “冬青小灰蝶”(holly blue)应为“冬青琉璃灰蝶”
- p. 262 “橙尖粉蝶“(orange tip)应为 “红襟粉蝶”,“绿纹白蝶”(green-veined white)应为暗脉菜粉蝶
- p. 264 “山地卷蝶”(mountain ringlet)应为黑珠红眼蝶;“草地褐蝶”(meadow brown)应为莽眼蝶;“小希思蝶”(small heath)应为潘非珍眼蝶
- p. 265 “紫色帝王蝶”应为紫闪蛱蝶
- p. 266 “希思豹纹蛱蝶”(heath fritillaries, Melilaea athalia),中文名和学名有误,应为“黄蜜蛱蝶(heath fritillaries, Melitaea athalia),原文中学名无误。
- p. 267 “纹黄蝶”(clouded yellow)应为红点豆粉蝶(colias croceus)

发表评论